“浙宗巧入者也,徽宗拙入者也。今讓之所刻,一豎一畫,必求展勢,是厭拙之入而願巧之出也。浙宗見巧莫如次閑,曼生巧七而拙三,龍泓(丁敬)忘巧忘拙,秋庵(黃易)巧拙均,山堂(蔣仁)則九拙而一巧。”
1
趙之謙在《書揚州吳讓之印稿》中,提出了巧拙之說:
“浙宗巧入者也,徽宗拙入者也。今讓之所刻,一豎一畫,必求展勢,是厭拙之入而願巧之出也。浙宗見巧莫如次閑,曼生巧七而拙三,龍泓(丁敬)忘巧忘拙,秋庵(黃易)巧拙均,山堂(蔣仁)則九拙而一巧。”
說得含混,試以解讀一下:
一、“入”應該是指創作入手所取的方法途徑,浙派入手巧,徽派入手拙;
二、拙之入、巧之出,是說創作人手“拙”,表現的面目“巧”;
三、所評浙派五人[注1]的巧拙,不是指入手的“巧”度,從“見巧”,“願巧之出”等,可以看出是指表現面目的巧拙程度;評五人不是評說“浙宗巧人”的問題,已換了概念。
這樣他褒拙貶巧的立論和目的比較能看清楚了:
一、浙派是巧入——巧出、拙出。而且從巧出、拙出的程度可以決定水平的高下。引至論斷趙次閑流為習尚,極為醜惡;
二、徽派是拙入——拙出。引至論斷吳讓之“厭拙之入而願巧之出”,所以才會見識低,去極力稱讚趙次閑,所以才會不懂自己篆刻的高妙,所以只能是二流印人,所以可以侮為“愚蠢”,所以可以“不必辯也”。
趙之謙才高氣盛,治經史詩文,擅書畫篆刻,自詡有“可供揮霍無虞中落”的天才,對篆刻,他有“今日由浙入皖幾合兩宗為一,而仍樹浙幟者”捨我其誰的“抱負”,(見後附魏錫曾文)這樣的心態,受到吳讓之對自己篆刻“而它皆非”的批評,反彈必定強烈而衝動。他祭起“褒拙貶巧”這似是而非的立論,以達到用貶趙來打吳這麼一個目的,就是這麼簡單、直接而且沒有風度。當然,後人從此文中發現有可探討的
印學問題,見仁見智,盡可發揮,這裡是說趙之謙立巧拙之論的始末。
大浪淘沙,逝者如斯。一部印學史,是要後人一代一代寫下去的。文明的腳步早已邁開,不可一世、想一個人說了算的時代,已決不會再現。
趙之謙說徽派是拙入拙出,拙出可以理解,表現的面目樸實簡拙。那麼“拙入”是什麼?用“樸實、簡單、稚拙(笨拙)”的手法來入手創作,就是“拙入”嗎?有“拙入”嗎?徽派是“拙入”嗎?下段試說之。
2
藝術者,心之美也,托諸形物,感動受眾。此是藝術的內涵和目的。
藝術者,技巧、手段也。“創機巧以濟用”,有巧思,有技術,方能“托諸形物”,方能表現“心之美者”,成為藝術。
巧與拙,書上有說是中國古典美學中,對立統一審美觀的經典。
中國道家哲學認為宇宙天地間“大音希聲”,“大象無形”,引申到具體為:“大直若屈,大巧若拙,大辯若訥”等。大巧若拙,有說是“真正靈巧的人,不自炫耀,表面上要好像很笨拙。”曾見文章強調,“好像”兩字不能易作老百姓說的“裝得”很笨拙,要很自然地表現得呆笨,才符合“大巧”,真是“佩服”之至。
哲學與藝術是姐妹,“大巧若拙”被引入藝術,論者說是“既高又神秘之境界”。
如真視此說為至理,那“大巧若拙”,也不是不巧就拙,更不是拙了才拙。而是說要使用巧思、機巧、精巧的技術手段,表現出樸素樸實的、古拙稚拙的意趣等等,又要不見巧的絲毫痕迹,才是最高明的。而且不能“裝拙”,硬裝樣,就像書法家寫兒童體了。
所以,在藝術創作中可能只有“巧入”而不存“拙入”的問題,只有“巧入巧出”或“巧入拙出”的形式美感的問題。
所以,凡習文藝必須要練基本功,要掌握技巧,“巧”門,開巧思,得巧悟,有了這才能去表現複雜的、豐富的、雋永的“心美”,或表現自然的、簡樸的、單純的“心美”。
當然掌握技巧說,不包括“新興人類”的“另類”“現代”“行為”等等藝術,不理解、不懂不能說。我們討論的是中國的傳統篆刻藝術不可能有“拙入”的問題。
3
對浙、徽兩派拙巧的問題,後來許多學者印家在《吳讓之印譜》趙、魏文後寫下了許多辯駁的意見。[注2]
任堇說:“其言辨也,而未備也。大抵學問之事求之與應,往往適得其反,抑跾跾巧拙者,徒以心為形役。純巧則纖,純拙則傖,誠不如兩忘之為愈也。”
高時顯說:“篆印以渾穆流麗為上,刻印以古茂圓轉為上,浙歟徽歟,胥是道歟。……各有所因,各有所創,初無所用其軒輊也。”“撝叔謂巧入、拙入似也,而未能索其源而觀其通也。”
曾熙說:“然完白山人(鄧石如)取漢人碑額生動之筆,以變漢人印用隸法之成例,蓋善用其巧也。丁、黃刀法取巧,然墨守漢印,固其善守拙也。”
吳昌碩說得最透徹:“余癖斯者既有年,不究派別,不計工拙,略知其趣,稍窮其變……。”好一個“不計工拙”不跾跾於巧拙,只緊緊抓住“趣”與“變”這篆刻藝術向前發展的大道理。葉一葦先生講,憑這個見識,吳昌碩的胸懷大大高過了趙之謙。
徽派沒有什麼“拙入”。從何震、程邃,到鄧石如、吳讓之,都是在印宗秦漢的旗幟下,“巧從機發”,找到某一個或幾個突破點,與古為新,自立家風。和浙派幾位大家一樣,都從“巧入”然後“巧出”或“拙出”,為篆刻藝術留下了瑰麗多姿的寶貴財富。拙與巧風格的表現,一個人、一個流派在不同時期、不同作品中都各會有體現,都是變化不定的,不能簡單地用來作界定的尺子。
趙之謙也是從“巧”入手走上成功之路的,他沒有走完,但已很傑出,他依靠金石學盛行發展的大環境,以自己的才力,在仿效鄧石如借鑒漢碑額篆入印的基礎上,更加擴大範圍,將古代各種金石文字和圖案,引進印面和邊款,技法也漸漸豐富成熟,推陳出新,創立了新風。他機巧過人,巧思過人,這從他的書畫印作品上都可以得到明鑒。所以,他篆刻自“巧入”是無庸置疑的。他的印作“巧入巧出”有之,“巧入拙出”有之,沒有什麼“拙入”,“裝拙”更無之。因為他太聰明了,天性總究難以掩飾。可惜他只活了五十五歲,如果天假以年,人書俱老,胸懷平和寬容,氣度更會不同,留在篆刻史上的形象會更完整,更輝煌。
王國維先生詞話雲,境由心造,“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,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”,李白有詩說: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飾”等等,都清楚明白又形象地道出了藝術創作的真諦,這才真正是有志於藝術者的座右銘。
趙之謙本身含混的巧拙之論,後來被許多人盲目引用,人云亦云,影響很大。試作一個分析和批評如上,供諸位參考。
注1:當時剛剛有人提出“西泠六家”之稱。趙之謙認為奚岡、陳豫鐘不入流,故不予置評。見黃惇《中國古代印論史》285頁注。
注2:以下引的評論,可查看西泠印社1981年版《吳讓之印存》,系名家原手跡影印。或查看韓天衡《歷代印學論文選》704頁起,西泠印社1985年出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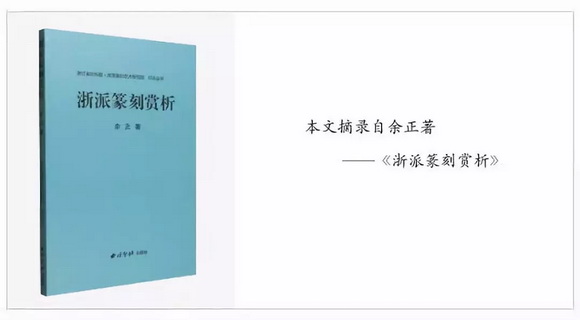
學習交流微信號:wenbaozhai365


